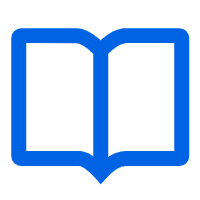苦苦菜花有啥功效?
天逐渐地暖起来,春的讯息越发明确,那田间地头、山岭沟壑、房前屋后的苦苦菜,早已按捺不住了,顶着土儿,争先恐后地钻出来。它在风中挺着绿色身子,舒展着叶片,沐浴阳光,好像一群淘气的孩子尽情地玩耍。
我们老家把这种学名叫做“苦苣菜”的野菜亲切地叫做“苦苦菜”。苦苦菜是春天里大自然赏赐给黄土地上人们的珍贵的绿色菜肴。它性寒味苦,可以清热凉血、健脾养肝,既可食用,亦可入药,对经常口舌生疮、口腔溃疡、大便燥结的人是绝好的自然良方。《本草纲目》记载:苦苦菜“久食,安心益气,实筋骨,明目。”说它久食可以安心气、壮筋骨和明眼睛,这是古人的智慧。
苦苦菜不仅在我们的餐桌上曾经扮演过很重要的角色,而且在我们的文学世界里也具有着重要的地位。《诗经·周南·谷风》中有这样一段脍炙人口的诗:“谁谓荼苦,其甘如荠。”这里的“荼”,指的就是苦苦菜。这里以荠菜(一种甜味野菜)和荼菜(苦苦菜)作比,用反诘修辞法,极言自己境遇的艰难和生活的愁苦。
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贫穷落后的年代,每到青黄不接的春荒季节,家乡人就靠这些绿的生灵来拯救饥饿。“雨前椿芽嫩如丝,雨后马齿韧如皮”,谷雨前天气湿润,雨水足,长在麦田里的苦苦菜鲜嫩异常,味苦而清香,是苦苦菜品质最好的时段。谷雨一过,天气渐热,雨水稀少,苦味更浓。
割苦苦菜最要紧的就是割根。割的时候要用镰刀贴着根部铲断,这样,下一茬苦苦菜就不再往高处长,一直匍匐在地,叶子也变得宽厚起来,产量和品质都有了保证。特别是第二茬苦苦菜,几乎成了麦田里独一份的青菜,成了牛羊的“口粮”。割苦苦菜一般是在麦收前两茬,第三茬割不割就由牛羊来主宰了。
割了苦苦菜先在井沿石上涮洗干净,再把叶子撕碎,菜心切成细条,用凉水泡上几个时辰,去却了“苦楚”,然后捞出来,控干水,拌上成盐、味精、醋、花椒油、辣椒油或小磨香油,甚至可以什么都不拌,蘸上蒜汁,美美地享受一顿,脆嫩清香,沁人心脾。或者用开水焯熟,过冷水,放入调料,凉拌食用,味道也很不错。我们过去还在玉米糁饭里蒸煮吃,蒸熟后,把苦菜掺到热饭里,饭香苦菜鲜,有滋有味。
若是在“大比之年”,把鲜苦菜在院子里晾晒干,入夏以后,收罢小麦,农闲时节,把苦菜用开水焯过,在凉水里浸上半个小时,捞出来,拧干,切成细丝,做“烂饭”。把小米和大豆或者小麦磨成的粗面合在一起“和面”,在案板上切成长条薄片,上蒸笼蒸熟,出笼晾后,过麻油,在大锅里和焯过的干苦菜一起小火翻炒,直到饭菜和匀,熟透为止。这种“苦菜烂饭”是农村人招待最尊贵客人的一道佳肴,也是一年里最奢侈的饭食。现在想来,这恐怕就是我们平陆人传统风味小吃“麻油凉粉”的前身吧,而且比“凉粉”更原生态和营养。
苦苦菜生命力极强,耐贫瘠,耐旱,可算是杂草类的“铁杆庄稼”,人们常常说苦菜“年年割,年年生”“割一茬长一茬”。记得过去母亲常常在“闲时”念叨一些富有哲理、朗朗上口的歌谣,在这中间,就有一首“割苦菜”歌:
割苦菜,要割根;
把根割,长着墩;
长着墩,鲜又嫩,
下顿又是一锅菜。
如今,岁月静好,粮食年年都大丰收,顿顿都吃白面馍馍,苦苦菜离我们的生活已经越来越远了。但在我心里,那漫山遍野的绿油